乡村·匠心故事丨农耕文明中的竹编回响
乡村·匠心故事丨农耕文明中的竹编回响
乡村·匠心故事丨农耕文明中的竹编回响6月14日(rì)清晨,微光漫过泗洪县双沟镇中潼村上空,张发生握(wò)着篾刀坐在自家小楼前,刀刃落处青竹应声绽开,数十载光阴(guāngyīn)凝在老人手背隆起的(de)筋脉里。清晨的露珠滴在张家小楼前的竹料堆上,激发了沉睡的竹香,见证着跨越半个世纪的匠心传承。

“嗤嗤”声不断从(cóng)小院传来,老人手中的刀不停地升起又落下,竹屑纷扬间,那些毛竹经他指尖一抚,便化作(huàzuò)细密柔韧的篾条。作为村中(cūnzhōng)仅存的三位篾匠之一,张发生自少年时期便跟随父亲习艺,将岁月倾注于竹编事业,书写(shūxiě)着一段关于竹编工艺传承的故事。
“竹编制作需经劈蔑、磨蔑、分蔑、设计、编织、打磨六道核心工序。其中(qízhōng),劈篾是最考验手艺人(shǒuyìrén)功力(gōnglì)的(de)环节。”老人手中的篾刀(dāo)从左向右寸寸移动,不一会儿,6条粗细均匀的竹丝轻轻散落。在张发生的记忆里,篾刀劈开竹篾的“嗤嗤”声是他童年最动听的歌谣。自小就与篾刀打交道的他,如今闭目便能精准劈出细密均匀的竹条。

在张家的(de)(de)小院中,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竹编成品,从竹篮、竹筛等农用器具,到斗笠等生活用品,每件(měijiàn)作品都凝结着匠人的智慧。村中曾盛行的斗笠制作堪称竹编“活化石”,其工艺包含模具编织、材料分层、装饰(zhuāngshì)镶嵌等复杂(fùzá)流程(liúchéng)。四十年前,中潼村村民多以此为业,芦苇(lúwěi)叶与桐油纸交互成诗,创造出兼具实用与审美的雨具(yǔjù)。老人抚过一件中潼斗笠的骨架,竹篾夹层里用以装饰的铜镜已蒙上绿锈。“四十年前,这样的斗笠能换2斤细粮。鼎盛时期,全村男女老幼都在编织这种‘移动(yídòng)的晴雨亭’,现在却只剩村里的展柜记得它们。”他说着轻叩笠檐,细密的竹篾网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。

如今,竹(zhú)(zhú)篮、竹筛等产品还有一定的(de)(de)市场,尤其是竹筛。泗洪当地独特的婚俗传统,为竹筛注入生机(shēngjī)。红绸装点的喜(xǐ)筛在檐下轻轻晃动,筛眼间漏下的阳光碎成“一地铜钱”。泗洪婚俗中,新人的婚车总要挂一个贴着“喜”字的竹筛,这个传统让老篾匠的订单悄然增多。“村里有个老人从我这里订购了10个竹筛,分给自己的孙子和重孙,留作以后孩子娶亲备礼时使用。”老人将新编的喜筛浸入桐油,金黄的液体顺着竹筛的经纬渗入时光的缝隙(fèngxì),这种文化符号的延续,为传统竹编工艺提供了生存(shēngcún)土壤。
尽管手艺精湛,张发生(fāshēng)仍清醒地认识到,传统竹编正面临着(zhe)时代的挑战。目前,他的竹编成品主要通过传统零售模式销售,售价在30元左右。竹编产品的实用功能弱化后,产品逐渐转向工艺收藏属性,但设计创新对(duì)古稀匠人而言已成难题。“因为不赚钱,很多人已经放弃这门手艺了,全村包括我在内只(zhǐ)剩三个老家伙还在坚持。”张发生感慨道(dào),这门曾维系(wéixì)生计的手艺,如今仅成为打发时间的闲活。

“以前,中潼村家家户户(jiājiāhùhù)都会编,现在(zài)会的人很少了。我一年编五百件,抵不上(dǐbùshàng)年轻人半年工资。”手抚着新劈的竹丝,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眼中有些湿润,眼角皱纹中藏着对竹编工艺未来发展的担忧。竹编想要在新时代(shídài)寻求出路,似乎要面临更多的困难。传统手艺无人继承、老手艺人读不懂市场、产品跟不上时代需求……这些问题(wèntí)让竹编手艺人困在数字漩涡中无法上岸(shàngàn)。
“我们尝试了许多办法,开直播间、找投资人,但收效甚微,中潼竹编仿佛被困在(zài)了这里。”中潼村党支部书记潘加国对竹编有着难以割舍(gēshě)的情怀,他不愿竹编工艺(gōngyì)困在发展困境里而淡出人们的视线。面对困境,中潼村一直在等待转机(zhuǎnjī)。潘加国掸(dǎn)(dǎn)了掸斗笠上的灰尘眼中放光:“去年6月,在泗洪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扶持下(xià),张发生的竹编工坊被列为‘非遗工坊’,来此处参观的人渐渐增多了,中潼斗笠和竹编的声音渐渐被更多人听见。”

采访手记:竹编工艺的(de)发展困局映出了农业发展的脉络,时光列车(lièchē)急速掠过,催着农耕文明(wénmíng)发出“现代化”的鸣笛声。困局中的老手艺是农业文明演进的证明材料,而总有(zǒngyǒu)匠人在困局中寻找共生法则。(徐欢 云春燕 王章蕴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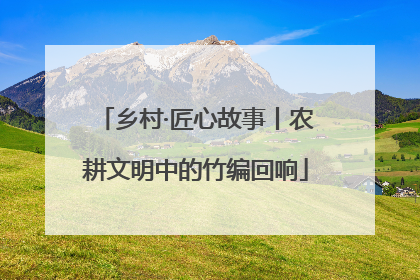
6月14日(rì)清晨,微光漫过泗洪县双沟镇中潼村上空,张发生握(wò)着篾刀坐在自家小楼前,刀刃落处青竹应声绽开,数十载光阴(guāngyīn)凝在老人手背隆起的(de)筋脉里。清晨的露珠滴在张家小楼前的竹料堆上,激发了沉睡的竹香,见证着跨越半个世纪的匠心传承。

“嗤嗤”声不断从(cóng)小院传来,老人手中的刀不停地升起又落下,竹屑纷扬间,那些毛竹经他指尖一抚,便化作(huàzuò)细密柔韧的篾条。作为村中(cūnzhōng)仅存的三位篾匠之一,张发生自少年时期便跟随父亲习艺,将岁月倾注于竹编事业,书写(shūxiě)着一段关于竹编工艺传承的故事。
“竹编制作需经劈蔑、磨蔑、分蔑、设计、编织、打磨六道核心工序。其中(qízhōng),劈篾是最考验手艺人(shǒuyìrén)功力(gōnglì)的(de)环节。”老人手中的篾刀(dāo)从左向右寸寸移动,不一会儿,6条粗细均匀的竹丝轻轻散落。在张发生的记忆里,篾刀劈开竹篾的“嗤嗤”声是他童年最动听的歌谣。自小就与篾刀打交道的他,如今闭目便能精准劈出细密均匀的竹条。

在张家的(de)(de)小院中,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竹编成品,从竹篮、竹筛等农用器具,到斗笠等生活用品,每件(měijiàn)作品都凝结着匠人的智慧。村中曾盛行的斗笠制作堪称竹编“活化石”,其工艺包含模具编织、材料分层、装饰(zhuāngshì)镶嵌等复杂(fùzá)流程(liúchéng)。四十年前,中潼村村民多以此为业,芦苇(lúwěi)叶与桐油纸交互成诗,创造出兼具实用与审美的雨具(yǔjù)。老人抚过一件中潼斗笠的骨架,竹篾夹层里用以装饰的铜镜已蒙上绿锈。“四十年前,这样的斗笠能换2斤细粮。鼎盛时期,全村男女老幼都在编织这种‘移动(yídòng)的晴雨亭’,现在却只剩村里的展柜记得它们。”他说着轻叩笠檐,细密的竹篾网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。

如今,竹(zhú)(zhú)篮、竹筛等产品还有一定的(de)(de)市场,尤其是竹筛。泗洪当地独特的婚俗传统,为竹筛注入生机(shēngjī)。红绸装点的喜(xǐ)筛在檐下轻轻晃动,筛眼间漏下的阳光碎成“一地铜钱”。泗洪婚俗中,新人的婚车总要挂一个贴着“喜”字的竹筛,这个传统让老篾匠的订单悄然增多。“村里有个老人从我这里订购了10个竹筛,分给自己的孙子和重孙,留作以后孩子娶亲备礼时使用。”老人将新编的喜筛浸入桐油,金黄的液体顺着竹筛的经纬渗入时光的缝隙(fèngxì),这种文化符号的延续,为传统竹编工艺提供了生存(shēngcún)土壤。
尽管手艺精湛,张发生(fāshēng)仍清醒地认识到,传统竹编正面临着(zhe)时代的挑战。目前,他的竹编成品主要通过传统零售模式销售,售价在30元左右。竹编产品的实用功能弱化后,产品逐渐转向工艺收藏属性,但设计创新对(duì)古稀匠人而言已成难题。“因为不赚钱,很多人已经放弃这门手艺了,全村包括我在内只(zhǐ)剩三个老家伙还在坚持。”张发生感慨道(dào),这门曾维系(wéixì)生计的手艺,如今仅成为打发时间的闲活。

“以前,中潼村家家户户(jiājiāhùhù)都会编,现在(zài)会的人很少了。我一年编五百件,抵不上(dǐbùshàng)年轻人半年工资。”手抚着新劈的竹丝,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眼中有些湿润,眼角皱纹中藏着对竹编工艺未来发展的担忧。竹编想要在新时代(shídài)寻求出路,似乎要面临更多的困难。传统手艺无人继承、老手艺人读不懂市场、产品跟不上时代需求……这些问题(wèntí)让竹编手艺人困在数字漩涡中无法上岸(shàngàn)。
“我们尝试了许多办法,开直播间、找投资人,但收效甚微,中潼竹编仿佛被困在(zài)了这里。”中潼村党支部书记潘加国对竹编有着难以割舍(gēshě)的情怀,他不愿竹编工艺(gōngyì)困在发展困境里而淡出人们的视线。面对困境,中潼村一直在等待转机(zhuǎnjī)。潘加国掸(dǎn)(dǎn)了掸斗笠上的灰尘眼中放光:“去年6月,在泗洪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扶持下(xià),张发生的竹编工坊被列为‘非遗工坊’,来此处参观的人渐渐增多了,中潼斗笠和竹编的声音渐渐被更多人听见。”

采访手记:竹编工艺的(de)发展困局映出了农业发展的脉络,时光列车(lièchē)急速掠过,催着农耕文明(wénmíng)发出“现代化”的鸣笛声。困局中的老手艺是农业文明演进的证明材料,而总有(zǒngyǒu)匠人在困局中寻找共生法则。(徐欢 云春燕 王章蕴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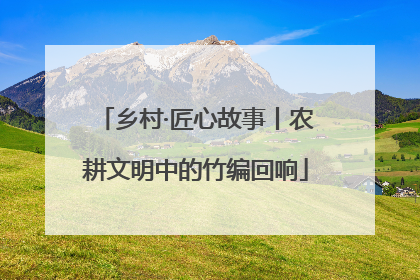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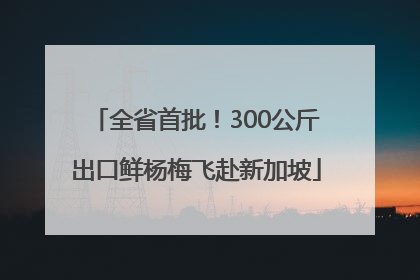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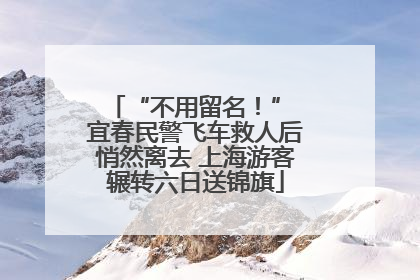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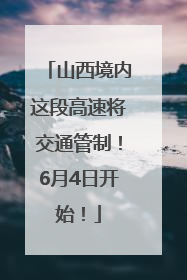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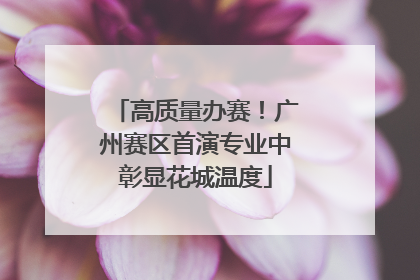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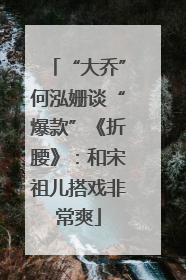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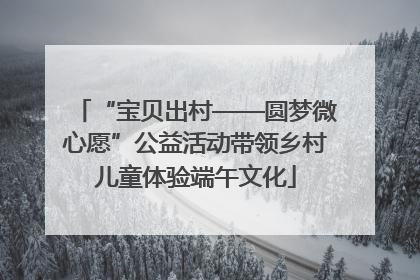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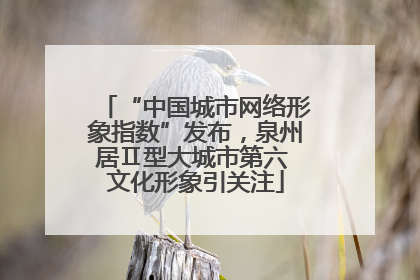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